以下文章《大家都不/读社论?── 报格、文化批判及其敌人》转载自
第六期《视角》人文评刊。
※谢伟伦 有人说,报纸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观察日记、人民的喉舌,新闻是报纸的身体。那么社论版无疑是报纸的灵魂,缺少了社论,与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无异。的确,“社论”(editorial)是一种经过肃穆、说理的观点或政策的揭露,代表报社独特的言论风格和评断时事的标准,针对事实和意见的精确、合理与有系统的陈述,藉以影响公众;也由于它揭示了报社的编辑方针和言论立场,故其成为各者之间最鲜明的区别。
有人说,报纸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观察日记、人民的喉舌,新闻是报纸的身体。那么社论版无疑是报纸的灵魂,缺少了社论,与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无异。的确,“社论”(editorial)是一种经过肃穆、说理的观点或政策的揭露,代表报社独特的言论风格和评断时事的标准,针对事实和意见的精确、合理与有系统的陈述,藉以影响公众;也由于它揭示了报社的编辑方针和言论立场,故其成为各者之间最鲜明的区别。
世界近代化、现代化的报纸缘起欧美。在17、18世纪的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突飞猛进,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法治国家逐渐成形,在法律保障和经济自主的条件下,各城市出现了专司传播信息、批评时政的新兴报业,其中的评论文章即可视为现代社论的雏形。18世纪下半业,革命风潮涌现,思想言论界百家争鸣,欧美遂进入“党派报业”(partisan journalism)时期,由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更为强化,有识之士多投身报业,往往身兼发行人、总编辑和主笔,全权主导社论,鼓吹一家之言;当时美国的报纸社论通常以一篇为限,刊载于头版,形同一个批判性论坛。这类报刊多由欧陆的学术性杂志及英国的政论性杂志演变而来,它们罕以营利为目的,反而以舆论的代言人和领导人自居。
当时中产阶级主导的国家体制在1830年代已告确立,报刊彼此遂从政治主张对立转变为报业竞争的关系,于是大众化的一分钱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冒现;而发行人开始以营利考量任命专人为总编辑和主笔,个人化报业(personal journalism)逐渐蜕变为制度化报业(institutional journalism),主笔的言论自主权减弱。就此时期的社论发展而言,葛雷利(Horace Greeley)在《纽约世界报》原本的社论版之外开辟了“言论对开版”,这项作法现已成为欧美报业的惯例。1950年代以后随着电视的普及,报业进入新的整并期,美国逐渐有一城一报的现象。报业为了尽可能取悦多数消费者,其政治立场更趋中立,社论也力求持平,避免向特定党派或人物过度倾斜。
捋虎须批龙麟 敢将文字照千秋
中文报业史上的社论则源于清末政论性刊物,但因为国家多难、制度纷乱,所以结构面上的时代特征或重要长进无甚特出,不过有两位人物倒不能不提。首先梁启超所撰写的社论鼓吹进步思想,臧否时政时人,在民国初年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力。民国四年袁世凯称帝,梁不计生死利害,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严厉批判,形成一股舆论风潮,堪称言论救国之表率。张季鸾本着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精神”,在20世纪上半叶坚守“文人论政”的信念,从《民立报》到主笔《大公报》,三十年间所写的评论不下三千篇,以三骂(吴佩孚、汪精卫、蒋介石)最脍炙人口,虽一无显位、二无钜资,却在中国报业史上永远留名。
作为解释脉络和议论新闻的“论说性文类”(expository-argumentative genre),梁启超对社论写作提出“公、要、周、适”四原则,突破文言文的窠臼,融合骈语、俚语、外语,笔锋常带感情,自成白话体例,以其所办《新民丛报》为名,曰“新民体”。他强调社论写作必须符合民意、论证严谨:“健全舆论云者,多数人之意思结合,而有统一性、继续性者也。非多数意思结合,不足以名舆论,非统一、继续,不足以名健全”,并说:“不健全舆论以瞽相瞽,无补颠扑,以狂监狂,只益于号呶”。约半世纪后,年仅35岁的金庸(查良镛)在《明报》初创时期亲笔撰写数以百万字计的社论,以文革前后几乎每天一篇的社评最具代表性。措词之严厉,一度引起林彪和江青不满却鞭长莫及;早年的《明报》因而被视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知识分子的报刊,赢得很高的清誉。
入戏的观众:批判作为一种志业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宏(Raymond Aron)长期在报社担任主笔,将自己的所思所想,用以分析社会结构,借着思想介入而改造现实,这个公案早已成为文化界的美谈。我们也不要忘了,马克思(Karl Marx)曾经短暂地当过记者,调查葡萄农人的景况,此举想必曾触动他胸中关怀被剥削者的左翼情怀。美国文学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当过战地记者,这种特殊的经历让一位作家的心灵拥有更大的腹地;甚至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也曾以记者为业,成名后还写过引人入胜的报导专书《智利秘密行动》。
这么多新闻人/文化人双璧合一的掌故,叫人何等心响往之!媒体报导公共事务,进而追求社会正义,创造公共利益,身为新闻人,原为尊严而光荣之事。记者信奉冷静客观、平衡报导,呈现事件“真相”,所以通常是不带价值判断的,是故在报社之中,资深记者、撰述委员所撰写的深度报导,或主笔所为文的社论、特稿,也就往往代表了立场的选择,和价值的认同,其中的理论评析,也成为文化思辩、集体追索的痕迹。就此,前《台湾日报》发行人司马文武更以“人的眉毛”来比喻报章社论,尽管作用有限,若摆对位置会有不一样的效果,至少可以改变形象和容貌,累积文字的影响力──如果社论能以理性负责的论述形式履行公共对话之天职,必然能在公共领域的重建工程中展现醒目的示范作用。
而这项工作注定是备尝艰辛的。作为报纸的读者,许多人总不免期待饱学深思、辩证清晰,又能发人所未见的论述出现,就这一点而言,除了娴熟的资料运用、各种社会力系谱的掌握外,我们比较不易在新闻人的笔下目击文采和史观。不知是否因为专业养成下的理性紧箍咒时时上身,通常我们看到的是,笔下不敢有情。报纸作为影响力作为广大的平面媒体,原可为社会文化教养的展示、教育场所,而今功能未见累增,未免还是可惜。此外或囿于篇幅和时效,许多报纸上的文章总一径快攻猛打,无心对议题深挖潜剖。
多年以来,马来西亚中文评论界始终少见一种把文字视为“社会实践载具”的批判:我们有真假参半的内幕,有辛辣的讽刺,有犬儒的嘲笑,甚或有激烈的否定,然而,或许由于基础的意识仍然缺乏,或许对人类仍缺乏同情与关怀,或许对民主精神仍欠理解,这样的氛围显然并不能负担一个民主时代诞生前应有的创造性角色。那么,创造性的评论文字,究竟在现阶段能创造些甚么?
要让这种本土论产生行动判断上的意义,就必须勇敢面对曾经影响这块土地的所有因素。在这个历史累积的结构性问题逐渐浮现的时刻,无论新经济政策、宗教信仰、社会正义或五一三事件,它们扭曲了族群关系,扭曲了宪政体制,扭曲了文化的元素,尤其严重的是扭曲了思考的方式。因此,创造性的社论或政论,不能只是“有意见,没主张”的浮泛之论,也不能单单只关切眼前的体制问题,而是要从最宏观的历史问题,到中程的体制问题,以迄最细腻的民主伦理等均有所注意,而且条理必须一致。于是往往可见,对某个问题是“反威权主义”,而对另一个问题则又是“威权主义”;对某个问题是“小政府主义”,另一个问题明显又是“大政府主义”观点。立场的混淆源自缺乏言论及思想的自由,由于自由的欠缺,自然缺乏了必须长期磨练反思才可能出现的“思想一致性”。其次,由于民主的胎动,民间力量的涌现,既有的社会形式早已不足承载新的社会内容。由“形式─内容”的辩证关系,马来西亚所面临的,其实已到了一个新“典范”(paradigm)取代旧“典范”的时刻,新的“典范”意味着需要新的语言,新的思考方式,才足以探讨新的问题,在新的视野里活跃。
语言负载思想,范畴决定视野,中文报章的定位及实践,却始终在质报(quality paper)与量报(quantity paper)的十字路口矛盾/摆荡。面对新科技、政经社会文化和量报风行等变局挑战,若不深刻思索、创研、实验与重构,以调查报导、精准新闻等应变方向,以内容上的“深度”优势,对抗网络的“速度”优势,恐怕不够格自诩为“精英办给精英看”或诉求的是“优质的读者”的报纸。
国有国格,报有报格,新闻与评论是一份报纸宣传的血肉,社论更如同一面旗帜,决定着报纸的政治面貌;做好了评论工作这一环,就能起着关键的引导作用,把全部报导工作贯串带动起来,因此报纸的评论工作应被看成是其思想定位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一点,近来传媒大亨梅铎(Rupert Murdoch)有意收购的《华尔街日报》、享誉全球的《纽约时报》都是个中翘楚。尤其前者,负责编写社论的全职人员高达40人,他们为《华尔街日报》《亚洲华尔街日报》和《华尔街日报欧洲版》编写社论及言论版文章,并负责编纂日刊《华尔街日报》“休闲与艺术”版内容,还为《华尔街日报》周末版提供书评、影评等各类重点评论和“品位”版内容,并为公司运营的“Opinion Journal.com”网站编写社论和言论文章。如此庞大的分工体系才能维持高质量的社论于不坠,与报业龙头《纽约时报》一样深刻影响美国文化界精英。
社论外包=新型分工=报格外包?
一般而言,讲求精实专业的中文报业均设有总主笔,其位阶与总编辑、总经理并驾齐驱。总主笔之下,有主笔、撰述员、特约撰述员各若干人,有的报社则设有社论委员会,由主笔、撰述员和社外的专家学者担任委员;总主笔每日会召开社论委员会商讨评论方针,再委由一名委员执笔。在我国报业史上曾有过这么鲜为人知的一段:茅草行动过后,沧海已变桑田,原任主笔的王锦发和黄友因被阻拦、无法重返复刊的《星洲日报》。这段大约两年的主笔“悬空期”,社论由编制外的人士“外包”,创下新页。
冀求经营模式转变的企业为能专注本身的核心技术、降低生产成本、经营弹性等因素,均把外包视为企业工作流程改善的万灵丹,但外包制度若未有详细的评选方法与紧密的控管机制相配合,不仅无法带来正面助益,更会对企业产生负面的影响。同样的,社论代表一家报社的立场和风格,若缺乏制度化的规划,贸然便宜行事予以“外包”,只会失去理性批判的力量,让中立持平沦为包装取悦消费者和权力当局的“专业惯例”,报格自然摇摇欲坠。
今日所发生的每一件新闻,都是未来的历史;而每一件现在的新闻,都和过去与未来互为文本,相互指涉,这也是新闻同历史一样具鉴往知来的作用。社论等同报纸的心脏,只有“异议”才是保持论述活力唯一可行的策略,可言应言而不言是失时,可言不当、应言不为是失言;一旦位置软化,批判的活力也就消失殆尽。若因驻留在“社论”或“新闻评论”的目光寥寥可数,就天真地断言:报纸新闻对社会变革(或变更)的影响,不在于社论写得多么铿锵有力,而是它对社会冲突性事件的渲染;那么,对文化理想的体会与深耕,对事件抱持的敏感和胆识,甚至是处理新闻如撰写历史的前瞻与谨慎,无疑是一大斫害──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场域,终将化作泡影。遗忘黑格尔的箴言,放弃坚持报格的良知,退守报导的正确与评论的专业,历史的荒谬剧必然周而复始;失却社会公器价值的报纸,不过是为虎作伥的工具,和“无知的载体”(ignorant agent),我们根本不需要偿付这样的代价。
Friday, June 29, 2007
[东方日报阉割社论之回响] 大家都不/读社论?
at
2:52 PM
![]()
Subscribe to:
Post Comments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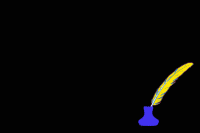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