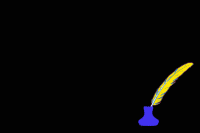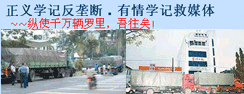以下文章《明天新闻自由行换形式照走! 参与者受促携国旗宪法黄丝带》转载自《当今大马》。 虽然昨日临时取消“新闻自由之行”,但是主办单位“勇敢自由媒体运动”(Benar)今日下午却又再宣布这场游行将如期举行,惟游行的形式却有所改变。(【点击媒体自由行主办单位:BENAR网站】)
虽然昨日临时取消“新闻自由之行”,但是主办单位“勇敢自由媒体运动”(Benar)今日下午却又再宣布这场游行将如期举行,惟游行的形式却有所改变。(【点击媒体自由行主办单位:BENAR网站】)
主办单位表示,参与者可以个别或两人一组,在上午9时30分至10时15分之间,“从任何方向和任何距离”,从独立广场走向全国报业俱乐部。
“记住,单独或两人一起行走是无需警方准证的。因此,在你走向全国报业俱乐部时,避免大群人在一起。”
这场活动原订于上午9时开始,参与者将个别或两人一组,向独立广场的国旗致敬,然后立即前往附近的全国报业俱乐部,以完成大约一公里的“新闻自由之路”。
独立广场行走破坏国家安全?
主办单位建议参与者,无论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驾车者,前往全国报业俱乐部都必须经过独立广场。
主办单位也表示,根据联邦宪法第10条文赋予和平集会权利,以及第9条文赋予的人身自由权利,阐明这场新闻自由行是人民的基本权利。
“我们看不到,为何在象征国家独立的独立广场上行走,会破坏国家安全?”
“我们呼吁参与者携带国旗或一份联邦宪法,以及扣上黄丝带显示你支持新闻自由。如果你是记者,请带上你的记者证。当你觉得有需要声明你的宪赋自由时,请挥动国旗,高唱国歌,引用联邦宪法第9或10条文,或援引国家原则尤其是第三项,即维护宪法。”
“让我们反映我国所出现的问题,即国民不能自由的在独立广场行走。我们每走一步都要问:没有新闻自由,国家独立所谓何物?”
代表“勇敢自由媒体运动”的独立新闻中心执行主任嘉雅特莉(V. Gayathry)昨日向《当今大马》证实,他们昨日会见警方后,最终以安全和交通为由决定取消“新闻自由之行”。她透露,来自金马区的卡迪柯彦(W Kharthikeyan)首席警长向他们表示,担心这场游行会引发安全和交通问题。
警方坚持申请准证却拒批发
根据主办单位今日在网站表示,警方在获得通知关于这场游行后,要求主办单位申请准证,但是却表明不会批发准证。
因此,主办单位决定不会申请警方准证,也不会取消这场游行,并以另一种形式进行游行。
不过,主办单位表示,虽然这个决定可能无法满足所有爱好自由的国民,但是却有必要做出变动,以便争取更多人和群体的参与。
这项游行活动是由公民组织“勇敢自由媒体运动”发起,目的是要讨论新闻自由和解除媒体限制等议题,并希望获得全国新闻从业员职工会(NUJ)、全国报业俱乐部和其他媒体组织的支持,以号召150名新闻从业员和公众参与。
首相署部长再益将在全国报业俱乐部针对新闻自由发表主题演说,并与媒体工作者对话。
点击阅读全文





 2001 年对华社而言,是迟来的世纪末。这一年的除夕夜,白沙罗华小被关闭,村民、家长和董教总从此展开艰钜而漫长的保校运动。也是这一年的5月28日,马华收购 南洋报业集团旗下的《南洋商报》、《中国报》和数十家杂志月刊。80多名中文评论人,展开“罢写”运动,拒绝投稿给已沦为马华党报的《南洋商报》和《中国 报》,以及涉嫌在幕后进行中文报业垄断的《星洲日报》。
2001 年对华社而言,是迟来的世纪末。这一年的除夕夜,白沙罗华小被关闭,村民、家长和董教总从此展开艰钜而漫长的保校运动。也是这一年的5月28日,马华收购 南洋报业集团旗下的《南洋商报》、《中国报》和数十家杂志月刊。80多名中文评论人,展开“罢写”运动,拒绝投稿给已沦为马华党报的《南洋商报》和《中国 报》,以及涉嫌在幕后进行中文报业垄断的《星洲日报》。 笔 者后来和众《南洋商报》和《中国报》记者与编辑展开仅维持数月的“反收购”运动(当然比起白小保校运动,算是不成气候的一鼓作气),之前声泪俱下的陈利良 不及一个月就淡出,黄伟益则由始至终都不肯参与,至于他们的理由,始终是个谜。八年后这两名当年感情丰富的新闻自由斗士,一个在槟州执政,一个甫入《东方 日报》就据说直升副总,如此顺利的际遇也同样接近谜。
笔 者后来和众《南洋商报》和《中国报》记者与编辑展开仅维持数月的“反收购”运动(当然比起白小保校运动,算是不成气候的一鼓作气),之前声泪俱下的陈利良 不及一个月就淡出,黄伟益则由始至终都不肯参与,至于他们的理由,始终是个谜。八年后这两名当年感情丰富的新闻自由斗士,一个在槟州执政,一个甫入《东方 日报》就据说直升副总,如此顺利的际遇也同样接近谜。 528 之前的《南洋商报》虽然在业绩上已开始落后于《星洲日报》和《中国报》,可是在内容上;尤其是政治、社会、人文和文学的报导和评论,正处于全盛时期,超越 了第一大报《星洲日报》。由当时的总主笔张景云开辟和主持的“景云沙龙”星期天特刊,由政治评论人黄进发和黄文慧记录撰文,后又由主笔陈美萍和刘瑞兰执 笔。“景云沙龙”对时事、政策、文化的讨论深度和广度,中文报界无人能出其右,在引导华社舆论上有呼风唤雨之势,远非当时“我出题,你作文”的“星洲广 场”所能相比。今天偶尔由星洲集团总编萧依钊客串采访的“星洲广场”与之相比,则简直像新闻学院实习生之作。
528 之前的《南洋商报》虽然在业绩上已开始落后于《星洲日报》和《中国报》,可是在内容上;尤其是政治、社会、人文和文学的报导和评论,正处于全盛时期,超越 了第一大报《星洲日报》。由当时的总主笔张景云开辟和主持的“景云沙龙”星期天特刊,由政治评论人黄进发和黄文慧记录撰文,后又由主笔陈美萍和刘瑞兰执 笔。“景云沙龙”对时事、政策、文化的讨论深度和广度,中文报界无人能出其右,在引导华社舆论上有呼风唤雨之势,远非当时“我出题,你作文”的“星洲广 场”所能相比。今天偶尔由星洲集团总编萧依钊客串采访的“星洲广场”与之相比,则简直像新闻学院实习生之作。 每 日评论方面,张景云、刘务球和陈美萍的社论,是铿将有力的报章公信力保证,而专栏评论的阵容,更是空前鼎盛;李万千、杨善勇、杨凯斌、庄迪彭、黄进发、陈 亚才等等,都是思想敏锐、掷地有声的健笔。《星洲日报》方面,或许当时只有潘永强、魏月萍、郑丁贤的阵容免强能与《商报》抗衡。
每 日评论方面,张景云、刘务球和陈美萍的社论,是铿将有力的报章公信力保证,而专栏评论的阵容,更是空前鼎盛;李万千、杨善勇、杨凯斌、庄迪彭、黄进发、陈 亚才等等,都是思想敏锐、掷地有声的健笔。《星洲日报》方面,或许当时只有潘永强、魏月萍、郑丁贤的阵容免强能与《商报》抗衡。 除 此之外,《南洋商报》还开辟了专为年轻人和学生运动而设的“新激荡”,政治改革的色彩非常鲜明。南洋报业被马华收购后,评论作者的罢写行动,既刻令每日评 论逊色不少,接著“景云沙龙”、艺术版、“新激荡”先后被腰斩,《南洋商报》的社会和人文气息大打折扣。再过数月,发起反收购的新闻从业员纷纷因意兴阑珊 或因馆方的白色恐怖手段而离职,副刊组“新视野”、专题组“新激荡”和主笔室众位出色的记者大部分从此在中文报界失去了“立锥之地”。(一些新闻从业员改 投打著反垄断旗帜的《东方日报》,结果也以丧失立锥之地收场,名单就省略了)
除 此之外,《南洋商报》还开辟了专为年轻人和学生运动而设的“新激荡”,政治改革的色彩非常鲜明。南洋报业被马华收购后,评论作者的罢写行动,既刻令每日评 论逊色不少,接著“景云沙龙”、艺术版、“新激荡”先后被腰斩,《南洋商报》的社会和人文气息大打折扣。再过数月,发起反收购的新闻从业员纷纷因意兴阑珊 或因馆方的白色恐怖手段而离职,副刊组“新视野”、专题组“新激荡”和主笔室众位出色的记者大部分从此在中文报界失去了“立锥之地”。(一些新闻从业员改 投打著反垄断旗帜的《东方日报》,结果也以丧失立锥之地收场,名单就省略了) 虽 然今天的中文网路媒体明显的在新闻和言论上更大胆、尖锐和开放,然而,比起曾经辉煌的《南洋商报》,似乎少了一分内省的人文气息。528之后,一份中文报 章在手,已经很少有“精神粮食”的感觉。《东方日报》言论和社论只有刘敬文独撑大局,多篇文笔不通的老人家评论或恶质的党棍文章,让该报声称的“给知识份 子看的报纸”定位显得啼笑皆非。不少人是看在附送The SUN和比《星洲日报》便宜,才勉强买一份,看看杨善勇、唐南发的专栏和专题组偶有的佳作。
虽 然今天的中文网路媒体明显的在新闻和言论上更大胆、尖锐和开放,然而,比起曾经辉煌的《南洋商报》,似乎少了一分内省的人文气息。528之后,一份中文报 章在手,已经很少有“精神粮食”的感觉。《东方日报》言论和社论只有刘敬文独撑大局,多篇文笔不通的老人家评论或恶质的党棍文章,让该报声称的“给知识份 子看的报纸”定位显得啼笑皆非。不少人是看在附送The SUN和比《星洲日报》便宜,才勉强买一份,看看杨善勇、唐南发的专栏和专题组偶有的佳作。 世 华媒体集团主席张晓卿于525在“第三届海外华文书市”分别为《星洲日报-历史,写在大马土地上》及《星洲日报研究》主持推介。后者作者彭伟步表示:“我 希望通过客观、公正的角度,全面反映星洲日报的历史及成就。”笔者如有机会拜读,倒是很想知道作者如何“客观”、“公正”的描述张晓卿通过国家机器,将南 洋报业这主要竞争对手吃掉的下流手段,又如何通过笼络知名海外作家、威迫和利诱国内优秀记者和文艺青年,来为其报业垄断的恶行包装。
世 华媒体集团主席张晓卿于525在“第三届海外华文书市”分别为《星洲日报-历史,写在大马土地上》及《星洲日报研究》主持推介。后者作者彭伟步表示:“我 希望通过客观、公正的角度,全面反映星洲日报的历史及成就。”笔者如有机会拜读,倒是很想知道作者如何“客观”、“公正”的描述张晓卿通过国家机器,将南 洋报业这主要竞争对手吃掉的下流手段,又如何通过笼络知名海外作家、威迫和利诱国内优秀记者和文艺青年,来为其报业垄断的恶行包装。 “香 港文化教父”梁文道则表示,他虽然远在香港,但也知道星洲日报过去有不少风雨争论,而《星洲日报-历史,写在大马土地上》这本书也要写在争论上。”至于甚 么“争论”,梁文道语焉不详。或许他的用词太客气了,去年一群《星洲日报》学记在报馆外示威时,星洲以载新闻纸的大罗厘挡驾血肉之躯的流氓行径(右图), 恐怕不能以“争论”淡化之吧?
“香 港文化教父”梁文道则表示,他虽然远在香港,但也知道星洲日报过去有不少风雨争论,而《星洲日报-历史,写在大马土地上》这本书也要写在争论上。”至于甚 么“争论”,梁文道语焉不详。或许他的用词太客气了,去年一群《星洲日报》学记在报馆外示威时,星洲以载新闻纸的大罗厘挡驾血肉之躯的流氓行径(右图), 恐怕不能以“争论”淡化之吧? 大 马人民在国家机器的宰制下,长期以来都无法写出一部真正客观反映各族群、各阶层建国贡献的国家历史,人民藉308的政治海啸给了政府一个教训,不仅希望政 府能以平等治国,也希望其正确看待各族群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如果星洲报业集团所撰写的中文报业历史,省略、歪曲、误读了528和后续事件,其罪行比歪 曲历史的政府更可恶,因为那是假借文化、华社和民间之名,对打压同行、欺骗读者、典当新闻和言论自由进行粉饰,中港台媒体学术界对这样的举动不得不小心。
大 马人民在国家机器的宰制下,长期以来都无法写出一部真正客观反映各族群、各阶层建国贡献的国家历史,人民藉308的政治海啸给了政府一个教训,不仅希望政 府能以平等治国,也希望其正确看待各族群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如果星洲报业集团所撰写的中文报业历史,省略、歪曲、误读了528和后续事件,其罪行比歪 曲历史的政府更可恶,因为那是假借文化、华社和民间之名,对打压同行、欺骗读者、典当新闻和言论自由进行粉饰,中港台媒体学术界对这样的举动不得不小心。 提到这点,又让我不得不重提旧事;8年前有人曾愿意赞助机票,让反报业收购和垄断的新闻从业员远赴香港,在世界中文媒体大会上说明马华收购的经过和星洲垄断的企图,结果没有一名反报业收购和垄断的新闻从业员知道有这样的机会,而唯一知道的人却淡出了反垄断行列。
提到这点,又让我不得不重提旧事;8年前有人曾愿意赞助机票,让反报业收购和垄断的新闻从业员远赴香港,在世界中文媒体大会上说明马华收购的经过和星洲垄断的企图,结果没有一名反报业收购和垄断的新闻从业员知道有这样的机会,而唯一知道的人却淡出了反垄断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