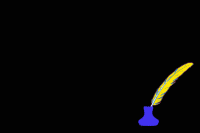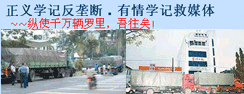以下文章《原来你们都是学记》转载自《当今大马》。
※杨白杨
59名《星洲日报》学生记者连署发表《星洲日报学记反垄断宣言》,促请张晓卿脱售所有南洋报业股权,让本地中文报业回到百花齐放的媒体生态,与言论自由、新闻专业接轨。宣言说:“我们正在捍卫一个社会的尊严。这是我们反垄断的信念。”
我看了连署名单,觉得很好笑,原来我所认识的黄进发、魏月萍、潘永强、庄迪澎、周忠信、林宏祥、陈慧思等等反垄断中坚分子,都是<星洲日报>的学记。改天我遇见他们,一定要大大声向他们喊道:“原来你们都是学记!”大声之后,我会小声的问:你们是自愿连署的吗?不是被人强迫连署的吧? 请不要怪我这样问,因为528报变时,90名评论人展开罢写反对马华收购南洋报业,正义的《星洲日报》刊登署名“小假”的文章,指真正想罢写的人数不到一半。他痛陈自己如何被逼加入罢写时说:“他们不仅通过电话、也通过E-MAIL等等各种方式,如排山倒海的来进行精神轰炸,炸到你不得不加入他们的行列为止。”
请不要怪我这样问,因为528报变时,90名评论人展开罢写反对马华收购南洋报业,正义的《星洲日报》刊登署名“小假”的文章,指真正想罢写的人数不到一半。他痛陈自己如何被逼加入罢写时说:“他们不仅通过电话、也通过E-MAIL等等各种方式,如排山倒海的来进行精神轰炸,炸到你不得不加入他们的行列为止。”
“小假”又说:“当时机来时,我会与其他被逼参与罢写行动的写作人站出来面对大家,面对华人社会,把写作人的良知发挥出来。”然而,五年半过去了,“小假”踪影不再,没有把良知发挥出来。《星洲日报》有此前科,当59个学记连署反垄断宣言时,人们自然会问,这一次,《星洲日报》会不会又弄个“大假”之类,自认是被逼连署的可怜虫,以污蔑连署的学记。 堂堂第一大报,本该带头捍卫新闻自由,在528事件中,即使真的没有涉及和政客勾结控制报业,看到评论人奋起反抗政党收购同行,都应该勇敢真诚地站出来,发挥报人的良知,和罢写的评论人同声同气,但是我们第一大报里的前辈们做了些什么榜样?他们和马华中央宣传局连成一气,撤谎污蔑罢写的评论人中有一半是被逼参与罢写。这些白纸黑字的谎言早被拆穿,他们还能够面不改容地三天两头高喊正义和温情,吹嘘他们的报人风骨,并继续掩盖反垄断的新闻,令人摇头,也让有自尊心的学记们面对罢写的朋友时,头都抬不起来。
堂堂第一大报,本该带头捍卫新闻自由,在528事件中,即使真的没有涉及和政客勾结控制报业,看到评论人奋起反抗政党收购同行,都应该勇敢真诚地站出来,发挥报人的良知,和罢写的评论人同声同气,但是我们第一大报里的前辈们做了些什么榜样?他们和马华中央宣传局连成一气,撤谎污蔑罢写的评论人中有一半是被逼参与罢写。这些白纸黑字的谎言早被拆穿,他们还能够面不改容地三天两头高喊正义和温情,吹嘘他们的报人风骨,并继续掩盖反垄断的新闻,令人摇头,也让有自尊心的学记们面对罢写的朋友时,头都抬不起来。
12月27日,《星洲日报》大事报导张晓卿和刘鉴铨的谈话,都在指责他人污蔑、丑化、谩骂和破坏《星洲日报》。隔日,59个《星洲日报》学记宣布连署反垄断宣言,难道又在污蔑、丑化、谩骂和破坏星洲日报了? 正告张晓卿和刘鉴铨,对付污蔑、丑化、谩骂和破坏,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些污蔑、丑化、谩骂和破坏公诸于世,就像反垄断人士时常把《星洲日报》对他们的污蔑、丑化、谩骂和破坏公诸于世,揭露《星洲日报》的真面目,最终使到《星洲日报》培养出来的59个学记站出来发表反垄断宣言,坚持反垄断信念,捍卫社会的尊严。
正告张晓卿和刘鉴铨,对付污蔑、丑化、谩骂和破坏,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些污蔑、丑化、谩骂和破坏公诸于世,就像反垄断人士时常把《星洲日报》对他们的污蔑、丑化、谩骂和破坏公诸于世,揭露《星洲日报》的真面目,最终使到《星洲日报》培养出来的59个学记站出来发表反垄断宣言,坚持反垄断信念,捍卫社会的尊严。 张晓卿和正义的新闻界前辈们,请不要指这59个学记是一小撮人,他们可不是第一大报里的“马大生”、“理大生”、“新山人”和“马六甲人”,当然也不是那个可怜兮兮被人强迫罢写还找不回良知的“小假”。他们的“一个名字是一个闪亮的生命”,不是躲藏在正义大印章后面的一具肉体。
张晓卿和正义的新闻界前辈们,请不要指这59个学记是一小撮人,他们可不是第一大报里的“马大生”、“理大生”、“新山人”和“马六甲人”,当然也不是那个可怜兮兮被人强迫罢写还找不回良知的“小假”。他们的“一个名字是一个闪亮的生命”,不是躲藏在正义大印章后面的一具肉体。
点击阅读全文
 此外,他们也呼吁视听人展现力量,用消费选择权向媒体老板传达最直接的讯息,
此外,他们也呼吁视听人展现力量,用消费选择权向媒体老板传达最直接的讯息, 从2001年至今,反对媒体垄断及政党拥有媒体的社会运动已经迈入第六个年头。
从2001年至今,反对媒体垄断及政党拥有媒体的社会运动已经迈入第六个年头。  但是,从马华公会的角度来看,它无需在此时将南洋报业脱售予张晓卿,因为下届大选的脚步已近,若根据砂拉越人联党在今年五月州选上演滑铁卢的成绩来看,下届大选必将为马华公会带来严峻考验。
但是,从马华公会的角度来看,它无需在此时将南洋报业脱售予张晓卿,因为下届大选的脚步已近,若根据砂拉越人联党在今年五月州选上演滑铁卢的成绩来看,下届大选必将为马华公会带来严峻考验。  再回顾张晓卿垄断中文媒体后的运动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激烈回应和否定反垄断运动。《星洲日报》总社前欲阻挡反垄断集会的两辆拖格罗里、《沟通平台》一系列对反垄断运动和网络媒体的污蔑与攻击、《南洋商报》一篇篇大加鞭挞刘瑞源的文章、《星洲日报》一则则张氏公会对张晓卿歌功颂德的报道等等,都反映了垄断集团的担忧与慌张。精明的百万读者只要稍有批判精神,不难嗅出其中的心虚与不安。
再回顾张晓卿垄断中文媒体后的运动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激烈回应和否定反垄断运动。《星洲日报》总社前欲阻挡反垄断集会的两辆拖格罗里、《沟通平台》一系列对反垄断运动和网络媒体的污蔑与攻击、《南洋商报》一篇篇大加鞭挞刘瑞源的文章、《星洲日报》一则则张氏公会对张晓卿歌功颂德的报道等等,都反映了垄断集团的担忧与慌张。精明的百万读者只要稍有批判精神,不难嗅出其中的心虚与不安。  从全国四地的反媒体垄断和平情愿活动、“黄丝带之约:与马华公会领袖喝茶救媒体”交流会,到黄丝带运动文章系列,我们看到站在运动前线的脸孔,除了五年前的老战友之外,还涌现了许多更有魄力、更富创意的学生与青年。
从全国四地的反媒体垄断和平情愿活动、“黄丝带之约:与马华公会领袖喝茶救媒体”交流会,到黄丝带运动文章系列,我们看到站在运动前线的脸孔,除了五年前的老战友之外,还涌现了许多更有魄力、更富创意的学生与青年。  垄断后的主流媒体预料将在2007年配合执政集团,大力营造国家独立50年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的假象;这出戏将一直唱到下届大选为止,为形势不妙的当政者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继续狼狈为奸欺骗读者。
垄断后的主流媒体预料将在2007年配合执政集团,大力营造国家独立50年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的假象;这出戏将一直唱到下届大选为止,为形势不妙的当政者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继续狼狈为奸欺骗读者。 
 刘瑞源是於11月26日在吉隆坡一家酒店举行“关于分售南洋报业股份以化解困境的献议”
刘瑞源是於11月26日在吉隆坡一家酒店举行“关于分售南洋报业股份以化解困境的献议” 不过,张晓卿较后於11月28日在出席砂拉越张氏公会成员到访甲清河堂张氏公会的一项欢送仪式后,受记者询问时,
不过,张晓卿较后於11月28日在出席砂拉越张氏公会成员到访甲清河堂张氏公会的一项欢送仪式后,受记者询问时, 刘瑞源在公开信中质疑黄平心“一个秘书,何德何能有资格超越主席,就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向名誉主席发出这样缺乏礼貌常识的最后通牒?” ,同时也直指张晓卿“不必在幕后,站出来当面解决吧”。
刘瑞源在公开信中质疑黄平心“一个秘书,何德何能有资格超越主席,就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向名誉主席发出这样缺乏礼貌常识的最后通牒?” ,同时也直指张晓卿“不必在幕后,站出来当面解决吧”。 虽然新海峡时报集团(NSTP)与马来前锋报集团(Utusan Malaysia Berhad)的合并计划仍箭在弦上,但我国媒体工业已逐渐被大规模的集团所控制乃不容否认之事实。这些集团依据本身的利益和策略形塑媒介的产制方向,随 著这股传播产业“私有化”的风气,传播与资讯体系日趋市场导向,愈来愈多的文化生产操控在大企业手中,不仅产生了社会资讯不平等的现象,更窄化甚至缩紧了 多元意见的出口。
虽然新海峡时报集团(NSTP)与马来前锋报集团(Utusan Malaysia Berhad)的合并计划仍箭在弦上,但我国媒体工业已逐渐被大规模的集团所控制乃不容否认之事实。这些集团依据本身的利益和策略形塑媒介的产制方向,随 著这股传播产业“私有化”的风气,传播与资讯体系日趋市场导向,愈来愈多的文化生产操控在大企业手中,不仅产生了社会资讯不平等的现象,更窄化甚至缩紧了 多元意见的出口。 我们不能忘记,传播也是一种解放性(liberating)的力量,藉由参与传播的过程,建立对话与实践机制,阅听人才能在无压迫的结构底下,享有作为一个 主体的权利。在整个传播系统中,阅听大众所存在的角色不只是消费者,还包括公民角色。换言之,媒体和阅听大众之间并不只是单纯的“卖方”与“买方”关系, 还包括如何透过媒体去展现其意见与生活的社会与文化权利。但在这场“反垄断”的战役中,批判报阀张晓卿及其媒体集团坐拥85%市场占有率,成了唯一的主旋 律,毕其功于此战役后,反观对中文媒体长期以来的内容、意识型态、伦理规范、新闻室民主等监督范畴甚少著墨,几乎存而不论。
我们不能忘记,传播也是一种解放性(liberating)的力量,藉由参与传播的过程,建立对话与实践机制,阅听人才能在无压迫的结构底下,享有作为一个 主体的权利。在整个传播系统中,阅听大众所存在的角色不只是消费者,还包括公民角色。换言之,媒体和阅听大众之间并不只是单纯的“卖方”与“买方”关系, 还包括如何透过媒体去展现其意见与生活的社会与文化权利。但在这场“反垄断”的战役中,批判报阀张晓卿及其媒体集团坐拥85%市场占有率,成了唯一的主旋 律,毕其功于此战役后,反观对中文媒体长期以来的内容、意识型态、伦理规范、新闻室民主等监督范畴甚少著墨,几乎存而不论。 经济学始祖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曾在其名著《国富论》对“劳工”下过定义:“广义的劳工包括一切体力和心力操作的人;狭义的劳工仅止于近代工厂、矿场或交通运输机构以体力换 取工资的人。”由此观之,新闻从业人员不论服务于报社、杂志社或电视台,负责编辑、采访、播音、文宣、印务、业务等劳心与劳力的受雇者,而非代表雇主行使 管理权的各级业务与行政主管人员,都符合广义的劳工定义。
经济学始祖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曾在其名著《国富论》对“劳工”下过定义:“广义的劳工包括一切体力和心力操作的人;狭义的劳工仅止于近代工厂、矿场或交通运输机构以体力换 取工资的人。”由此观之,新闻从业人员不论服务于报社、杂志社或电视台,负责编辑、采访、播音、文宣、印务、业务等劳心与劳力的受雇者,而非代表雇主行使 管理权的各级业务与行政主管人员,都符合广义的劳工定义。 我国自80年代以来,拼经济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与迷思,几乎全面指导著产、官、学的思维与论述,影响所及是“经济优先”、“稳定发展”、“使用者付费”等的 论调甚嚣尘上;以掩人耳目的“竞争力”之名,行削减“社会安全与福利”保障之实。主管劳动事务的机构人力资源部也三番两次的表明“中间”立场(不偏劳方也 不偏资方),完全依法行事,这样的立场,看似谨守了文官中立的原则,但却暴露出行政体系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性质与社会关系的无知与漠视。
我国自80年代以来,拼经济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与迷思,几乎全面指导著产、官、学的思维与论述,影响所及是“经济优先”、“稳定发展”、“使用者付费”等的 论调甚嚣尘上;以掩人耳目的“竞争力”之名,行削减“社会安全与福利”保障之实。主管劳动事务的机构人力资源部也三番两次的表明“中间”立场(不偏劳方也 不偏资方),完全依法行事,这样的立场,看似谨守了文官中立的原则,但却暴露出行政体系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性质与社会关系的无知与漠视。 “阶级是人们在其走过的历史中间定义出来的。”英国史学巨擘汤普森(E.P. Thompson)在其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里反覆论证:阶级是行动和关系的历史过程,为阶层研究及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两方面,提供一向重要的批判, 并指出阶级意识是阶级经验的文化表现。除了媒体社会运动,从学校落实媒体劳工意识的教育扎根工作,纳入“工会与劳动意识”的相关知识与认识,传授学生当面 对老板恶意解散如何争取自身权益,以及平时参与工会争取新闻自由空间等等,让传播学院所传授的知识,不再只是帮助媒体企业培养工作生力军,而更进一步得以 具备就业时保护自我以及主动争取权益的能力,毋宁是非常重要的。新闻品质、专业素养、媒体环境与劳动条件这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有优良的劳动条件与 工作环境,新闻品质与专业素养才能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媒体环境始能够获致改善,而媒体内容的提升亦不远矣。
“阶级是人们在其走过的历史中间定义出来的。”英国史学巨擘汤普森(E.P. Thompson)在其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里反覆论证:阶级是行动和关系的历史过程,为阶层研究及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两方面,提供一向重要的批判, 并指出阶级意识是阶级经验的文化表现。除了媒体社会运动,从学校落实媒体劳工意识的教育扎根工作,纳入“工会与劳动意识”的相关知识与认识,传授学生当面 对老板恶意解散如何争取自身权益,以及平时参与工会争取新闻自由空间等等,让传播学院所传授的知识,不再只是帮助媒体企业培养工作生力军,而更进一步得以 具备就业时保护自我以及主动争取权益的能力,毋宁是非常重要的。新闻品质、专业素养、媒体环境与劳动条件这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有优良的劳动条件与 工作环境,新闻品质与专业素养才能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媒体环境始能够获致改善,而媒体内容的提升亦不远矣。 前路漫长且遥远,在这个关键时刻,改革团体或许可以从在意识型态的“阵地战”当中,取得舆论支持、进而持续批判张晓卿的媒体集团,但并不必然带来运动的顺 境;从欧美或台湾抗争经验中,参照各种媒体识读、媒体监督和媒体改造等理论上的优势与论点的精辟,展现出长远恢弘的建制与格局,可能是一条突破困境的道路。
前路漫长且遥远,在这个关键时刻,改革团体或许可以从在意识型态的“阵地战”当中,取得舆论支持、进而持续批判张晓卿的媒体集团,但并不必然带来运动的顺 境;从欧美或台湾抗争经验中,参照各种媒体识读、媒体监督和媒体改造等理论上的优势与论点的精辟,展现出长远恢弘的建制与格局,可能是一条突破困境的道路。
 阿末扎希说,媒体合并将使阅读率降低,因为他们都是拥有相同的读者群,而这将让两家媒体面对损失。
阿末扎希说,媒体合并将使阅读率降低,因为他们都是拥有相同的读者群,而这将让两家媒体面对损失。 《独立新闻在线》总编辑庄迪澎强调,公民知情权和媒体垄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维护阅听人的知情权、了解实情的真相的基础就是达到媒体的多元。他解释说,当我们接受媒体报道的新闻可能是与事实不符的,阅听人需要通过不同的媒体来辨认真相,了解事实。
《独立新闻在线》总编辑庄迪澎强调,公民知情权和媒体垄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维护阅听人的知情权、了解实情的真相的基础就是达到媒体的多元。他解释说,当我们接受媒体报道的新闻可能是与事实不符的,阅听人需要通过不同的媒体来辨认真相,了解事实。 庄迪澎指出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知情权是不可或缺的。他以民主选举来说明知情权的重要性,一个国家拥有自由的媒体才会有民主的选举。
庄迪澎指出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知情权是不可或缺的。他以民主选举来说明知情权的重要性,一个国家拥有自由的媒体才会有民主的选举。 新纪元媒体系讲师傅向红,首先就提出知情权在隐私以及公共课题方面,其实相当模糊,尤其是对于针对公众人物。
新纪元媒体系讲师傅向红,首先就提出知情权在隐私以及公共课题方面,其实相当模糊,尤其是对于针对公众人物。 黄进发认为国家的机密法令应该有清楚地界定、规定文件,以免机密法令被政府滥用。
黄进发认为国家的机密法令应该有清楚地界定、规定文件,以免机密法令被政府滥用。 《资讯自由法令》联盟是在2004年,由人民之声(SUARAM)召集而成立的联盟。当时,独立新闻中心(CLJ)被选为秘书处,同时联盟也草拟出《资讯自由法令》10大原则。
《资讯自由法令》联盟是在2004年,由人民之声(SUARAM)召集而成立的联盟。当时,独立新闻中心(CLJ)被选为秘书处,同时联盟也草拟出《资讯自由法令》10大原则。 2001 年5月28日,谦工业(Home Industries)宣布以2忆3012万4961零吉或每股5零吉50仙,脱售南洋报业72.35%股权予华仁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全国第二大执政党、 拥有百万党员、声称代表马来西亚华社的马华公会,不顾以董教总、雪华堂、校友联总、华研等为首的数十个华团所提出的反对收购立场,以商业投资为由来合理化 整个收购计划。马华公会牺牲的华社的利益,还假借民主之名召开特大,企图通过2千余名马华代表的投选?合理化收购南洋的行为。
2001 年5月28日,谦工业(Home Industries)宣布以2忆3012万4961零吉或每股5零吉50仙,脱售南洋报业72.35%股权予华仁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全国第二大执政党、 拥有百万党员、声称代表马来西亚华社的马华公会,不顾以董教总、雪华堂、校友联总、华研等为首的数十个华团所提出的反对收购立场,以商业投资为由来合理化 整个收购计划。马华公会牺牲的华社的利益,还假借民主之名召开特大,企图通过2千余名马华代表的投选?合理化收购南洋的行为。 当 初被置疑涉及收购行动的星洲集团,曾经在2001年5月30日在报上作出声明反击谣言。到了今天,马华议决出售南洋报业股份予张晓卿,隔天张晓卿旗下的4 大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及《光明日报》同样的也不约而同刊登他的声明,以“张晓卿家族与南洋报业股权表”,力证星洲媒体集团没涉及 收购南洋报业,企图把张晓卿从星洲媒体集团中切割出来。然而吊诡的是,批评者事实上从一开始都只是针对握有控制权的张晓卿及替其负责统筹的极高层,何以《星洲日报》整体主动的和个体捆绑在一起?
当 初被置疑涉及收购行动的星洲集团,曾经在2001年5月30日在报上作出声明反击谣言。到了今天,马华议决出售南洋报业股份予张晓卿,隔天张晓卿旗下的4 大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及《光明日报》同样的也不约而同刊登他的声明,以“张晓卿家族与南洋报业股权表”,力证星洲媒体集团没涉及 收购南洋报业,企图把张晓卿从星洲媒体集团中切割出来。然而吊诡的是,批评者事实上从一开始都只是针对握有控制权的张晓卿及替其负责统筹的极高层,何以《星洲日报》整体主动的和个体捆绑在一起? 11月3日对其他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但对于我们一群反对媒体垄断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常的大日子。事因我们曾经同步参与在《星洲日报》总社、 槟城办事处及新山办事处三地的静坐请愿。从5年前的反收购运动到现在的反垄断运动,我们不仅获得以前反收购前辈给予的支持,也看到了许许多多年轻人和大专 生朋友们自发的出来参加,争取媒体独立自由的重任可说是薪尽火传。我们的坦荡荡,对比《星洲日报》用两辆载满刘鉴铨所谓的反垄断信念的罗里,阻挡在写着 “正义至上,情在人间”总社大门前,反而突显了我们的反垄断信念更具正义!
11月3日对其他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但对于我们一群反对媒体垄断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常的大日子。事因我们曾经同步参与在《星洲日报》总社、 槟城办事处及新山办事处三地的静坐请愿。从5年前的反收购运动到现在的反垄断运动,我们不仅获得以前反收购前辈给予的支持,也看到了许许多多年轻人和大专 生朋友们自发的出来参加,争取媒体独立自由的重任可说是薪尽火传。我们的坦荡荡,对比《星洲日报》用两辆载满刘鉴铨所谓的反垄断信念的罗里,阻挡在写着 “正义至上,情在人间”总社大门前,反而突显了我们的反垄断信念更具正义! 紧 接而来的“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是“反垄断和平请愿”的延续,本来是向马华要求出售其剩余南洋报业股份予非支配性买家,以及呼吁马华议员支 持专司媒体法律改革的国会特选委员会/议员连线。可惜的是,马华竟然在官方网页上窜改活动名称,更只字不提媒体垄断与政党拥有媒体的议题。马华在这媒体垄 断与政党拥有媒体的课题上的采取模糊不清的立场,避重就轻地回答出席者的提问,这一种没有担当、不负责任、没有远见的危机处理方式,如何能不遭受他人的批 评?希望我们能在“黄丝带之约”召集人向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发表的公开信中得到马华的重视及认真回答所提出的7个问题,请不要让我再次失望。
紧 接而来的“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是“反垄断和平请愿”的延续,本来是向马华要求出售其剩余南洋报业股份予非支配性买家,以及呼吁马华议员支 持专司媒体法律改革的国会特选委员会/议员连线。可惜的是,马华竟然在官方网页上窜改活动名称,更只字不提媒体垄断与政党拥有媒体的议题。马华在这媒体垄 断与政党拥有媒体的课题上的采取模糊不清的立场,避重就轻地回答出席者的提问,这一种没有担当、不负责任、没有远见的危机处理方式,如何能不遭受他人的批 评?希望我们能在“黄丝带之约”召集人向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发表的公开信中得到马华的重视及认真回答所提出的7个问题,请不要让我再次失望。 最新一期的《大马商业》(Malaysian Business)双周刊,以封面专题方式报道中文媒体大亨张晓卿的为人处事,并通过访问他身边的人士,大赞他的低调作风以及对中华文化与华教的热爱。
最新一期的《大马商业》(Malaysian Business)双周刊,以封面专题方式报道中文媒体大亨张晓卿的为人处事,并通过访问他身边的人士,大赞他的低调作风以及对中华文化与华教的热爱。 最明显的是《新海峡时报》,它於10月27日突然冒出一篇专文,大篇幅描绘张晓卿如何“从胶工到媒体大亨”(From rubber tapper to media mogul)。这篇由《新海峡时报》记者刘美珊(译音,Lau Meisan)撰写的文章,着重描绘张晓卿如何从1988年收购《星洲日报》开始,在少过20年的时间内崛起成为媒体大亨的奋斗史。
最明显的是《新海峡时报》,它於10月27日突然冒出一篇专文,大篇幅描绘张晓卿如何“从胶工到媒体大亨”(From rubber tapper to media mogul)。这篇由《新海峡时报》记者刘美珊(译音,Lau Meisan)撰写的文章,着重描绘张晓卿如何从1988年收购《星洲日报》开始,在少过20年的时间内崛起成为媒体大亨的奋斗史。
 自张晓卿通过Ezywood Options私人有限公司,向马华投资臂膀华仁控股收购21.02%的南洋报业股权的消息于10月17日传开以来,民间反对张晓卿以一人之力独掌总共占据本地中文报业85%以上市场份额的4大报章之反垄断呼声开始酝酿、发酵。
自张晓卿通过Ezywood Options私人有限公司,向马华投资臂膀华仁控股收购21.02%的南洋报业股权的消息于10月17日传开以来,民间反对张晓卿以一人之力独掌总共占据本地中文报业85%以上市场份额的4大报章之反垄断呼声开始酝酿、发酵。 常常,我们都陷入一个思维盲点,总下意识的认为新闻从业员是对政府官僚和其他公众人物施加舆论压力的人,却没想到新闻从业身为涵盖公共事务领域的行业,其参与者和工作者也必须接受同样标准的公共舆论之检测。
常常,我们都陷入一个思维盲点,总下意识的认为新闻从业员是对政府官僚和其他公众人物施加舆论压力的人,却没想到新闻从业身为涵盖公共事务领域的行业,其参与者和工作者也必须接受同样标准的公共舆论之检测。 谁说没有呢?原来诉说优点的都被刊登了出来,诉说缺点的都被压了下来!慢慢的,我开始听到身边一些写专栏的朋友,传来一些可怕的消息,凡文章触及报业垄断说词的都被退稿。我吓了一跳,原来一份背负着责任让广大群众了解真相的报纸,可以掩盖事实。原来那曾经教我要据实报道,接受多方意见的指导者,可以盖着一边的耳朵, 假装听不到反对的声音。
谁说没有呢?原来诉说优点的都被刊登了出来,诉说缺点的都被压了下来!慢慢的,我开始听到身边一些写专栏的朋友,传来一些可怕的消息,凡文章触及报业垄断说词的都被退稿。我吓了一跳,原来一份背负着责任让广大群众了解真相的报纸,可以掩盖事实。原来那曾经教我要据实报道,接受多方意见的指导者,可以盖着一边的耳朵, 假装听不到反对的声音。 坊间都知道,南洋报业集团属下的生活出版社出版多本杂志。它跟国内其他同时出版多份杂志和三日刊的出版社一样,旗下杂志品种多,赚钱的话就办下去,亏本的话就关掉。
坊间都知道,南洋报业集团属下的生活出版社出版多本杂志。它跟国内其他同时出版多份杂志和三日刊的出版社一样,旗下杂志品种多,赚钱的话就办下去,亏本的话就关掉。 当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及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说,“南洋报业被收购事件,却让星洲日报被某些人士套上垄断的帽子,有关的指责一是指垄断大马中文报章的市场,二是指垄断言论空间。不论是第一项指责或第二项指责,其实都是对垄断的错误认知所导致”,我不由得想,刘鉴铨说自己反对垄断,却又不支持反垄断运动,是不是对垄断和反对垄断运动的错误认知所致?
当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及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说,“南洋报业被收购事件,却让星洲日报被某些人士套上垄断的帽子,有关的指责一是指垄断大马中文报章的市场,二是指垄断言论空间。不论是第一项指责或第二项指责,其实都是对垄断的错误认知所导致”,我不由得想,刘鉴铨说自己反对垄断,却又不支持反垄断运动,是不是对垄断和反对垄断运动的错误认知所致? 张晓卿一人坐拥二山,占据了马来西亚六份全国性中文报章的四份报章,其竞争者《光华日报》及《东方日报》一者主攻北马市场、影响力有限,一者仍旧在起步阶段、销售网有待建立,未能普及郊区乡镇,比较起来宛若大树与蜉蚁。报章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广告,张晓卿收购南洋后,可以套餐形式推销四报广告,让广告商以优惠价同时在四份报纸打广告,削弱竞争者的广告吸引力,中文报广告市场从此听凭张氏指挥是指日可待的事。市场落差加上现实限制及政治偏见,这两个小玩家就连体面地生存下来也成问题,又何须谈什么通过价格、品质、技术、产品创新、行销策略来争取消费人的购买?
张晓卿一人坐拥二山,占据了马来西亚六份全国性中文报章的四份报章,其竞争者《光华日报》及《东方日报》一者主攻北马市场、影响力有限,一者仍旧在起步阶段、销售网有待建立,未能普及郊区乡镇,比较起来宛若大树与蜉蚁。报章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广告,张晓卿收购南洋后,可以套餐形式推销四报广告,让广告商以优惠价同时在四份报纸打广告,削弱竞争者的广告吸引力,中文报广告市场从此听凭张氏指挥是指日可待的事。市场落差加上现实限制及政治偏见,这两个小玩家就连体面地生存下来也成问题,又何须谈什么通过价格、品质、技术、产品创新、行销策略来争取消费人的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