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丝带运动文章系列(六)
作者:mksow(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委员) 吴海瑚的大作“需要他们时,他们在那里?”。我们来检验一下。看完全文,你会发现,所有的主旋律,还是支持星洲朋友们反驳或攻击批评者的回声四式。或许你会问,这什么四式是什么东东?
吴海瑚的大作“需要他们时,他们在那里?”。我们来检验一下。看完全文,你会发现,所有的主旋律,还是支持星洲朋友们反驳或攻击批评者的回声四式。或许你会问,这什么四式是什么东东?
第一式,贴。贴什么?标签。没有任何反驳理由,把批评者归类。例如,批评者都是“妒嫉破坏”,“别有居心”,“另有动机”,又或者是“背后有其他势力在操弄”。如何得出以上结论?很遗憾,没讲。反正只要你批评我,请从以上罪名找个位子坐。文章中另一个显著的例子,吴批“民主民权和一言堂都是依他们自己喜好来下定义”。问题是,“民主民权和一言堂不依他们喜好的来下定义”的那个定义是什么?没讲。民主民权和一言堂怎样被他们依自己喜好来下定义?也没讲。什么都没讲,怎样证明他人是依喜好来下定义?由此观之,以上所有指责从来都只停留在表面,没有推论过程,更别说挑战过批评者对垄断的论述。
反垄断不曾批判过新闻从业员
第二式,绑。绑什么?群体。没有被批评的群体,都被绑架以制造同仇敌忾的氛围。例如,“这不是国内新闻从业员的错...”。问题是,我们几时有说过“这是新闻从业员的错”?我们反垄断运动什么时候有批评过新闻从业员?没有。事实上,对刘鉴铨,许春,萧依钊或星洲的任何人都好,我们从来只有爱的呼唤,没有恨的怨怼,我们甚至欢迎刘鉴铨来领导我们反对张晓卿。所以,吴海瑚为什么会认为我们会认为新闻从业员有错?他是从那里知道的?  第三式,比。比什么?烂。以他人的错误,来合理化自己的错误。例如,“对巫统辖下另一集团控制媒体..有过什么表示?..”。事实是,我们一向来都有表示,我们一路来都有动作。承蒙四合一大媒体集团对此没有报导,所以没有人知道是正常。我原谅吴海瑚对此事的无知。更何况,一个人没有对巫统表示过,是不是就代表没有资格对张晓卿表示?答案很清楚,不是。因为,如果你答是,这个世界永远找不到一个有资格的人。烂,可以无限的比下去,没有尽头。
第三式,比。比什么?烂。以他人的错误,来合理化自己的错误。例如,“对巫统辖下另一集团控制媒体..有过什么表示?..”。事实是,我们一向来都有表示,我们一路来都有动作。承蒙四合一大媒体集团对此没有报导,所以没有人知道是正常。我原谅吴海瑚对此事的无知。更何况,一个人没有对巫统表示过,是不是就代表没有资格对张晓卿表示?答案很清楚,不是。因为,如果你答是,这个世界永远找不到一个有资格的人。烂,可以无限的比下去,没有尽头。
第四式,搞。搞什么?族群意识。扬起族群大旗,大搞民粹来掩烂。这是这一波反击攻势的主招式。主要动作有:1.在族群内建构危机意识,树立一个面目模糊的狄夷假想敌,企图制造团结的氛围;2.以大中华文化为饵,挑拨族群的大中华情结,试图把焦点转移。所以,当吴海瑚写下“他们只敢对同肤色的社群喊话,不敢向外人吭声!”这种高族群意识,非理性,毫无营养,无关争议点,但却极煽惑人心的文字时,隐藏在其背后的潜台词已经非常明显。
好了。看清楚了吧?贴,绑,比,搞。四招齐发,模糊焦点,转移主战场。不仅完全没有对反垄断者的论述有过任何的反驳,也完全没有提出一套为自方辩护的论述出来。这样的反驳论述,可以过关吗?可以吗?不。我不接受。
你烂,他比你烂,所以不算什么 第二位,叶宁(右图)。“谁在表达正义?”。光明日报的报总编辑写了这一篇文章。看完全文只有一个感觉,老样子,没有拼论述,没有比道理。还是跳脱不出贴,绑,比,搞,四招式的范围之内。
第二位,叶宁(右图)。“谁在表达正义?”。光明日报的报总编辑写了这一篇文章。看完全文只有一个感觉,老样子,没有拼论述,没有比道理。还是跳脱不出贴,绑,比,搞,四招式的范围之内。
叶宁的第一招,先比烂。“懒散的前同事,金钱挂帅的前上司:...这些和反垄断的论述有什么关系?原谅我的不客气,从文章中,叶宁显露出一个可怕的认知-身份资格比道理论述更重要。再推深一层,我们可以得出她的潜台词-虽然我烂,但比我烂的人没有资格批评我;你烂,他比你烂,所以你的烂不算什么。
呜呼哀哉。我难过。当年畅饮黑狗啤,豪气干云,巾帼不让胡髯的英雌,那里去了?我庆幸。幸好查卡利亚没搞媒体,不然报纸上的查卡利亚一定也会被描述成没犯什么错的好议员。
一招使完后,接下来第二招,绑。可怜的新闻工作者,再次被动的,不知情的被推上前线。事实是,反垄断运动的朋友们从来没有怨怼你们,没有批评你们,没有置喙你们,没有针对你们。对于新闻工作者,我们从来只有谅解,只有体恤,只有呼唤,只有敬礼,只有尊重。真的。对于新闻工作者,在反垄断的课题上,我们有的只是期盼,没有任何的强求。
拉了群体到一个没有炮火的地方表演了反击之后,开始发出第三招-贴。原谅我,叶女侠,我不得不问。叫骂?在那里?抹黑?在那里?示威没人了解?从何得知?欺善是永恒的旋律?从何得知?全部没有过程,只有判词。这样的反驳论述,可以过关吗?可以吗?不。我不接受。
大卿帝国四式用老,5年不曾进步 “贴,绑,比,搞”,大卿帝国现在仅有的四式。这四式对普罗大众,没什武功的朋友来说,或许还有点扰惑的作用。但是,招式用久了,来来去去都是那四下,终会有被大家看破的一天。从曾毓琳,舒庆祥,吴海瑚,叶宁等等的文章看来,经过五年的长期论战,他们终究还是跳脱不出这个框架。这究竟是因为没有竞争和压力,所导致的论述大退步?还是大家慑于职权名利,经已失去自主提出另一种声音的权力?我不知道。
“贴,绑,比,搞”,大卿帝国现在仅有的四式。这四式对普罗大众,没什武功的朋友来说,或许还有点扰惑的作用。但是,招式用久了,来来去去都是那四下,终会有被大家看破的一天。从曾毓琳,舒庆祥,吴海瑚,叶宁等等的文章看来,经过五年的长期论战,他们终究还是跳脱不出这个框架。这究竟是因为没有竞争和压力,所导致的论述大退步?还是大家慑于职权名利,经已失去自主提出另一种声音的权力?我不知道。
末了,吴海瑚说他听到狗吠,叶宁投诉有人在嚎叫。嚎叫?狗吠?或许有时间,我们要问问吴海瑚和叶宁,请他们说详细些,他们真的确定声音是从对方那里传出来,而不是自家的回声?
编按:为揭露官商垄断媒体之恶果,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邀请老中青三代评论人撰写系列文章。本系列文章同步刊登于《当今大马》、《独立新闻在线》、《黄丝带》及各大中文网站论坛。
此文章《卿帝国的回声四式》转载自《当今大马》。
Saturday, November 11, 2006
[黄丝带] 006 卿帝国的回声四式
at
7:02 PM
![]()
Subscribe to:
Post Comments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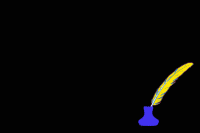




















3 comments:
争骨牌
争骨牌
张晓卿终于「光明正大」的吃掉了南洋商报。或许因着这个缘故,最近的反媒体垄断运动似乎干扰了许多人的清梦,终于勉强抖动一下黏了五年的睡眼,惺忪朦胧的问:「啥事啊?」
只是,半睡半醒状态,接下来的阶段,若不是继续倒头大睡,可能就是梦游。到头来,还是在沉睡。
有人问我:「若张晓卿不买南洋,还有谁会买南洋?」也有人说:「弄一个执照开新报馆,总比收拾南洋的摊子来得划算。」更有人说:「给张晓卿收购,总好过给巫统收购。」
当历史只剩下饭后话题的资格以及水准,人们对事情真相的认真态度或者关心,也就只有这种程度。而,若要长篇大论的把事情解释清楚,谁得空听?谁要听?
一群愚民的心理,只要以适当的权利高度以及力度的干预,就能随心所欲地左右其骨牌倾倒模式。民若不愚,他们就不会是任由摆布的骨牌。若有人要抵抗或制衡这种权利耍弄,他们所能做的,很可能就只有以另一种高度和力度来干预这骨牌阵。到头来,几乎就是两派法师在一群没脑子的僵尸阵之中斗法。
反媒体垄断,若要争取一群缺乏公民意识的百姓来支持,最起码并且务实的,或许就只有争取他们乌合之众的支持和呐喊。要获得他们的支持,就要赋予他们种种漂亮感人的口号和皮相。要他们知晓反垄断的意义,在缺乏资源以及历史意识严重断层的处境下,这恐怕会是奢望。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许多人对这事件的看法,多半只有对张晓卿或星洲日报的「挺」或「倒」而已。对于「媒体操守」或「新闻自由」,这些反而是次要,甚至一点都不重要。这多少说明为何张氏帝国拥趸们的维护手段,总是习惯于歌功颂德。那些时评人的批判言论,在许多看客读者眼中,其中卖点恐怕就只有张氏帝国是怎么衰、怎么烂、怎么「乞人憎」。而新闻自由如何在张氏帝国的作为下受威胁,或者这种手段所表现的族群思维如何对国家社稷的发展构成负面效果,这些似乎都不重要。
针对张氏帝国的批判,也牵引了一些人士「顺便」把对友族的偏见一并骂进去。这就好象张三在街上踩蕉皮跌倒,却归咎于李四在十二层楼如厕后抽水一般。这种「顺便骂」的现象,可能是基于趁着「同仇敌忾」的机会顺便吼叫一番,可以制造出暂时性的「同心合一」的表象。然而,这也表现出大众对事情前因后果的理解依然倾向于标签判刑,缺乏理智的分析能力。甚至可以这么说:华人群体在分辨真伪时,肤色根据可能比理念原则更重要。
报章对一些人而言,只不过是用来「观赏新闻」用的。也有一些则是为了解读看客消费市场,从时事动态中寻找发财机会。张氏帝国的庞大,自然使得许多攀其阴影的寄生植物获得肥料。若如斯自肥已经满足了他们对「安居乐业」的定义,媒体被垄断又有啥值得大惊小怪的?即使要闹,也许就如我的友人所说的「总好过给巫统收购」而已。肤色毕竟是最方便又廉价的天平标准。
一个缺乏公民意识的「ma/ess population」,他们所需要的媒体,自然是「ma/ess media」。
垄断媒体的恶行,以及纵容如此行径的恶法,当然要受口诛笔伐。只是,在反对声浪之中,总让我怀疑,到底有多少巴仙是凑热闹的看客。即使赚得他们的同声呐喊,在长远的新闻自由征途上,他们的风雨同路依然是痴人梦话。
也许,习惯就好。
转贴自Window of Minerva's Owl http://windowofminerva.blogspot.com/
洞里的无知,洞外的无奈 ?? 柏拉图千年的感叹
我在大学一年级时买过一本书:《政治学导论》。凡此类书,每讲至政治哲学时,必提及柏拉图的《理想国》。而此书作者是这样总结他的:柏拉图的过失在过于极端。他竟然抱着让统治阶级和军人们可以共享财产与妻子这样令人发指的想法 (outrageous idea)。
后来,自己读《理想国》,发现有个问题贯穿整本书:为什么非正义的人总比正义的人要过得好?更确切地说,这本书在我看来,就是柏拉图为了解释为什么苏格拉底会被处死这个问题的思考成果。
我读《史记》,每读至,心中总不解。何以如此才华洋溢,鞠躬尽瘁者,竟落得投江自尽,英年早逝的结果?每读至,心中总有强烈压迫感。何以令匈奴闻风丧胆者,竟‘无尺寸之功以得以封邑’?或许很多上班族会问:为什么我勤勤恳恳,加班加点,最后升值加薪的却总是别人?学生会问:为什么自己的默默耕耘,却总比不上那些能说会道的同学受老师赏识?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好人为什么总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似乎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疑惑。我们现代人对私利的愤愤不平,自然无从体会先贤们内心的痛苦;更不会有太史公这样的胸襟与眼光为他们立传,或柏拉图那样的学识为之著书立学。我们忙得只会对怀才不遇的人施舍一声叹息,然后心中暗自庆幸,还好自己的际遇没那么差。
《理想国》的对话开始没多久,Thrasymanchus 就已经把这个困扰人类千年(并且我相信还会继续困扰我们)的问题提了出来。而Adeimatus 和Glaucon, 虽然他们自己很想相信正义,但现实中绝对正义的人如此之落魄,而貌似正义,实则卑劣的人却如此受人、神之爱戴,使他们很难说服自己去相信正义是可以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考虑任何利害关系而本身值得去追求的一种品德。
既然要试图解释为什么不正义的人总要比正义的人幸福,就必须先搞清楚正义到底是什么。《理想国》此卷开头列举了两个当时盛行的讲法:(一)正义是给予一个人他所应得的;(二) 正义是强者的利益。然而这两种说法都一一被柏拉图用他一贯的手法推翻了。我认为这种方法有诡辩的成分,因为总感觉他是在一步一步带领我走到他早已中意的结论,所以我不能完全被他所信服。不论如何,既然这不是他所认为的正义,且让我们看看柏拉图所谓的正义为何物?
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每个人一生只做上天所赋予他最适合做的那份工作。他把个人和城邦都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像金子般的部分是头脑及其所具备的理性思考的能力;像银子般的部分是精神;而最等而下之的是欲望,柏拉图把它比喻成铜或铁。相对于一个城邦来讲,监护者就是它的头脑;辅助者/军人是它的精神;剩下的农民和商人是它的欲望。在接受了柏拉图所设计的教育后,头脑和监护者就会拥有知识。经过理智思考,就会做出明智的判断,所以,这个个人和这个城邦就会是有智慧的。精神和军人是头脑与监护者天然的盟友。只要他们在任何艰苦条件,或强烈诱惑下,都遵守理智所下达的命令,那么,这个人和这个城邦就会是勇敢的。欲望是最不理智也最危险的部分。但只要他们自律,和前两者达成共识:谁该主宰,谁该服从,那么个人和城邦就会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与团结。而使这三者都规规矩矩做自己的本分,不越位的德行,柏拉图称之为‘正义’。说白了,‘正义’对于柏拉图来说就是孔老夫子的那句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如此一来,个人就会获得内心的平静,与之相随的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个体。他不需要医生,更无需法官,因为他自身已拥有‘正义’,无需外人替他判定是非。城邦不会有阶级斗争,更不会爆发内战。它是一个绝对团结的城邦。用时下流行的话说,也许就是‘和谐社会’。这就是柏拉图所谓的‘正义’的人和‘正义’的城邦。如此‘正义’的内在组织自然会产生正义的行为,而这正义的行为反过来又会维持‘正义’的内在组织。就好像一个身心健康的人自然会从事健康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又有助于他维持自身的健康一样。
理清了柏拉图对正义的定义,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类人的下场总是不尽如人意。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把另一个关键词:形式 (Form), 搞清楚。柏拉图认为我们感官世界所能看到的,摸到的都不是真的事物。他们千变万化,稍纵即逝。唯一真实的是它们背后永恒不变的形式。这个形式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它只是以一种概念存在于哲学家的脑海中。任何感官世界里的事物都只是它们的映像。用柏拉图自己的例子:神只创造了一张床。它只拥有一张床之所以能称之为一张床的最基本的东西。这就是一张最完美,最理想,最真实的床。它只存在于天上或被有智慧的人看到,却绝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顶多也只是接近于这个形式。一个木匠所制作出的床是床这个概念的效仿,它绝不可能和床的形式完全符合。正如我们画一个正方形,但它的四边绝对不可能毫厘不差得相等,四角也绝不可能不多不少都是90度,所以现实生活中没有真正的正方形,真的正方形只是一个概念。以此推断,上述正义的人和正义的城邦都是人和城邦最理想的状态,是它们的形式和概念,是人之所以能称之为人,城邦之所以能称之为城邦的条件。柏拉图在书中对他们的描述以及他对理想国细节的规划在他的理论里的确是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他自己也在书中承认‘理论和实践是不可能一致的,所以不要执意让我证明我们理想国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得到实现。’ 因此,那些批评柏拉图不现实,甚至极端可怕的学者是没有把这本书读懂。
也许你会问:这又怎么能解释苏格拉底的死和非正义的人总比正义的人过得好的问题呢?答案就在于柏拉图那个洞穴的比喻。我们自小就活在一个山洞里。我们的腿和颈项都被固定住了,使我们的视线只局限于前方的大屏幕。后面的火与远处的光把事物及其声音和动作投影在屏幕上。我们以为哪些映像都是真实的事物,从不对之怀疑。直到有一天,他们中的其中一位挣脱了桎梏,爬到了洞外。强烈的阳光使他不得不紧闭双眼。但慢慢的,他开始习惯看东西在地上的影子、然后看它们在水中的倒影、然后看它们的本身。最后,他抬头看到晚上的星星和月亮,直到他敢于直视太阳??那个在感官世界中给予人类视觉与一切事物能够被看到的第三个元素,即它们的源头。他豁然开朗,警觉原来以前自以为真实的东西都是虚假的。他为自己感到庆幸,与此同时也为那些还在洞里执著于虚假事物的伙伴们而惋惜。于是,他回到洞里,讲述他的经历并试图带领他们走向真实的世界,但因为不能马上适应洞里的黑暗,他注定会显得像个傻子。于是人们都认定出洞是毫无价值的尝试,因为他比出洞前更傻,更怪了。那些对虚假映像解释得头头是道,被公认为有智慧,有学问的人会借机来抨击他。如果他对真理坚信不移,并执意要拯救他的伙伴,他会被冠以败坏青年的恶名,或其他更严重的罪刑。苏格拉底对于柏拉图来说应该是这样一位出了洞的哲人。当他走出感官世界,进入理智空间,他看到了一切事物的形式。又或许他已看到了给予人类智慧和一切形式的第三个元素??那个犹如感官世界中的太阳的善。他认定这就是真理,并试图教育他所遇到的人,但他却被那些无知又固执的伙伴们猜疑并憎恨,最终被民主制的希腊城邦给处死了。
有些人天生拥有哲学的头脑。在经过教育和训练后,会比其他人更容易看到事物的形式。 当他们看到人和城邦最理想的状态后,他们首先会努力使自己接近于这个‘人’的概念。于是,他们就成为了柏拉图所说的‘正义’的人。如果有机会,他们会把自己看到的城邦的概念付诸实施,使之变成一个‘正义’的城邦。但苏格拉底的经历告诉他们这将是极其艰难的,并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另一方面,在看到了真理后,他们又不愿意再和洞里的人‘同流合污’。于是,在那些不‘正义’的‘智者’、‘学者’继续接受人们的爱戴与敬仰时,他们过着并不应当属于他们的孤独生活。没有地位,没有名誉,甚至没有对他们聪明才智,学识涵养的肯定。按柏拉图的设想,他们应该成为哲学王;应该致力于使自己的城邦和城邦里的人民都变得‘正义’;应该生前拥有人们授予的荣耀;死后被人们所怀念。他们应该是最快乐,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使整个人民和城邦都快乐,幸福。
这就是我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找到的答案。为什么苏格拉底这样的人会被处死?为什么非正义的人总比正义的人过得好?柏拉图为之作了哲学的回答,但这最终还是个心理问题,是个寻找心理平衡的问题。你可以说‘正义’的人是快乐的,因为相对于人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来讲,头脑对知识的追求是绝对,无污染的快乐,而‘正义’的行为得以维持他们自身‘正义’的内在组织,这本身就是件极幸福的事。但这却并没有解决这个心理问题。我想那些出了洞的人看见洞里人的无知与愚昧,一定感到痛心疾首,而对于自己的无能为力,又感到无可奈何。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与维持自身的‘正义’是否就能抵消他们内心的苦闷?所以,柏拉图最后不得不自我欺骗道:如果正义的人在生前遭遇不幸与苦难,那最终都是为他们好。一切行为都逃不过神的眼睛。不正义的人,就算他们年轻时得以躲避惩罚,他们最后也还是会罪有应得受到羞辱。而正义的人,则会在有生之年获得应有的名声与回报,死后会获得灵魂的不朽。柏拉图如此安慰自己。
屈原、贾生的洞察远见,李广将军的带兵艺术,都没有为他们赢得应有的回报。太史公为李陵说话,却因此遭受极刑。心中疑惑难以自疏,故发愤著书,以通其惑。然时招至嘲笑与不解。所以,太史公说他书中的微言大义‘难为浅见寡闻道也’,而只愿‘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屈原、贾生的洞察远见不为人所理解,李将军的带兵艺术不为人所欣赏,不是因为他们怪,而是因为我们笨;是我们长期在洞里所形成的目光短浅,心胸狭窄。我不知道时下的上班族是怎么想的,至少在我周围的大学生从来都不怀疑自己所拿到的那个‘A’ 是否实至名归;他们从来都认为自己得到的‘C’ 是对自己的不公平。我们对自己的愚昧全然不知,以为有个博士、教授名堂的人所讲的都是知识与智慧,但他们却可以告诉我们柏拉图的想法极端,可怕。他们在讲堂上故作高深,我们在讲堂下问些自以为聪明的问题。大家都以为在进取,殊不知我们都只是在照着好学生、好老师的映像依样画葫芦。时间久了,都以为自己是好学生、好老师了。我们都被表象给骗了,都以为看到的映像是真实的。我们都以为各科拿‘A’的就一定是好学生;奖学金得主就一定是人才;有个博士、教授名堂的人就一定有相应的学识涵养。我们都在洞里相互欺骗,自得其乐。出了洞的人笑看我们的无知与愚昧。看着洞中虚假的欣欣向荣,无奈地思考着两千多年前柏拉图所思考的问题。
中国古人对明知道别人比自己贤德却还坐在他应坐的位子上谓之‘窃’。我们却从来不怀疑自己是否该得到那个‘A’与否。我们只满足于自己混到了一个‘A’、一个学位,一个硕士、一个博士。然后自我肯定为一个大学生、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我们使尽浑身解数演绎着那些表象,因为那是达到目的的必要手段,是我们拿‘A’,拿学位,达到洞里人公认为成功的必然手段。一时间,好像人人都成了马基雅弗利笔下的邦主??表面正义凛然,爱民如子,实则这是他维护政权的基本要素。然而,当遇到一个默默耕耘却没有无懈可击的成绩单的学生,或一位具备真才实学却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堂的人时,我们不是施舍声怀才不遇的叹息,就是不给予他们任何肯定。那一声叹息也许还会带给他们某种心灵上的安慰,然而多数人都不认为他们的不幸是不幸,才是他们真正的不幸。
柏拉图这么重视理智,把理性思考的能力比做金子。然而理性思考、逻辑推断却解决不了这人类千年的疑惑。他的感叹,穿越时间和空间,依然也将继续在人类心中找到共鸣。然而却始终没找到所需的那个平衡。也许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太史公在他《悲士不遇赋》中的那句话:理不可据,智不可持。
傅蓉
回应:“争骨牌”
听君一席话,真是点到一直埋在我心头的迷思。自反垄断思潮激起的当儿,我发现要让一般民众跟得上长篇大论的现象分析并给与积极的态度共同在思想上交流,似乎太高估大家的公民意识了。我的一班大专朋友,论及与报纸的亲密接触,多数是偶尔才在咖啡店随意翻一翻桌上沾了油渍的报纸,然后煞有其事的跟你说:喂,giant的厕纸很便宜!媒体自由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如不曾听过的新外星球名号,要不然就是与林吉祥有关系的反对党专用名词。
当然,这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必须长掌握整体的客观分析与核心拿捏,对此我也自认贫乏不足。但至少,喊起反垄断的口号时,人们应该清楚自己行动背后的理由,而不是如君所言的“凑热闹”。
文末“也许,习惯就好”这一句话,感觉就像面对极为不争气的群体大众时,无奈中叹一叹,安慰自己。我相信这蕴藏在许多关心此事的人心中。处于此势,到底大家能做些什么?付出的努力,大家可否有把握?
杂乱的因缘当中,教育可谓重要的一环,但该从何下手?
-LH-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