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文章乃针对《光明日报》总编辑叶宁刊登于《光明日报》文章《谁在表达正义?》的回应。
没有人敢声称自己代表正义,包括让人景仰的前美国总统林肯。
多年来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则关于林肯的轶事:
在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位将领向忧心忡忡的林肯说道:“总统,您放心,我们的军队一定能打赢这一场仗,因为真理站在我们这一边。”不过,林肯却回答道:“我不在乎真理是否站在我们这边,我所关心的是,我们是不是站在真理那一边。”
所以每当我看到星洲日报的口号“正义至上,情在人间”时,我就心惊胆跳,我就想到林肯的话。
没有一个发起和参与反对媒体垄断集会的人宣称过自己是正义之士,我们表达反媒体垄断的立场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贤人政治,我们不相信儒商救国、救民族的“出师表”。
我们只相信制度,尤其是一个能够确保各中文报皆会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消费群和广告商家,而竞相打擦边球,报导更多民间关心的所谓“敏感议题”,揭露更多被当权者和利益集团掩盖之时弊的报业市场。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一方独霸和坐大的报业市场,其市场竞争机制能鞭策新闻从业员和媒体业者不断的试探和推进当局对新闻报导管制的底线,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编采自主以及新闻自由的空间! 我们不信什么以优秀的中华文化来团结起来的中文报业能够整合各方力量,来为中文社群立言请命的漂亮说辞,如果这种话可以成立,那么这个世界最优秀的中华文化在中国,在更久远的汉唐盛世,请问在这些拥有最优秀,或相对比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文化更优秀的时代和地域的大众传播媒介,有做到真正的为广大的草根群众立言请命的责任吗?
我们不信什么以优秀的中华文化来团结起来的中文报业能够整合各方力量,来为中文社群立言请命的漂亮说辞,如果这种话可以成立,那么这个世界最优秀的中华文化在中国,在更久远的汉唐盛世,请问在这些拥有最优秀,或相对比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文化更优秀的时代和地域的大众传播媒介,有做到真正的为广大的草根群众立言请命的责任吗?
我们信不过个人、我们信不过优秀的文化、我们信不过商人的经济理性、我们信不过还没开诚布公的交流就在己方的百万读者媒体上抹黑异见人士的报纸、我们也信不过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有没有徇私的一天,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之中,在国家的公权力之间,还有媒体与媒体之间,建立起没有任何一方独大的监督制衡机制。
我们要更多更开放、容许全方位交流的沟通平台,让多方回响交流碰击,让我们兼听则明。这样,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个组织都能尝试表达他(们)认为是正义的声音。
因为我们清楚明了,兼听则明时,虽然我们未必就表达了正义,抑或掌握了正义;但兼听则明时,我们正在向正义的标杆挺进。
Friday, November 10, 2006
兼听则明时,我们才能趋近正义!
at
7:47 PM
![]()
Subscribe to:
Post Comments (At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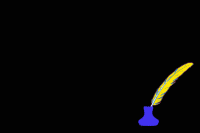




















3 comments:
关于这个课题,请恕我摘录一小段潘永强的评论,作为反垄媒体断议题的注脚。
海耶克(F.A. Hayek)曾批????制?致思想的?有化,其?,政????合?????,后果也不遑多?,必然????的??化。?可以指??,?然可以指??棍、指?文棍,以及指?言?。因此,要追求健全?步的社?,不是??一?正??大的?人,而是促成???力相?的魔鬼,互相??。?正??人的?情,才是民族?步的象徵。
?史的教?是,?普天之下只剩一??人明君?,??人不??得更加仁慈,反而??以?率土之?,都莫非是自己的王土王臣,最后必定跋扈傲慢?所欲?,??暴君流氓,?道今日???不是如此?
言?新?不?一派?霸
要???人自由?利,就不能指望?人,惟有扶起??魔鬼互施妖法,才能透????生制衡。把?力分成不同的碎片,用野心?制野心,才可以?造分歧中的均?。小?生即使用英文???理,也懂得彩虹?非只有一道?色,?有多元色彩,?能在天空?出明?彩?,何?是言?新?,更不??由一?一人?霸??。
以?一?江山唯我?尊,不?是?力的意淫。
??《彩虹?非只有一道?色》? 文/潘永?
关于这个课题,请恕我摘录一小段潘永强的评论,作为反垄媒体断议题的注脚。
海耶克(F.A. Hayek)曾批评极权体制导致思想的国有化,其实,政党与报阀合谋垄断报业,后果也不遑多让,必然带来舆论的党产化。党可以指挥枪,当然可以指挥报棍、指挥文棍,以及指挥言论。因此,要追求健全进步的社会,不是拥护一个正义伟大的圣人,而是促成两个实力相当的魔鬼,互相对?。对正义圣人的无情,才是民族进步的象征。
历史的教训是,当普天之下只剩一个圣人明君时,则圣人不会变得更加仁慈,反而会误以为率土之滨,都莫非是自己的王土王臣,最后必定跋扈傲慢为所欲为,沦为暴君流氓,难道今日实况岂不是如此?
言论新闻不应一派独霸
要维护个人自由权利,就不能指望圣人,惟有扶起几个魔鬼互施妖法,才能透过竞争产生制衡。把权力分成不同的碎片,用野心牵制野心,才可以创造分歧中的均势。小学生即使用英文学习数理,也懂得彩虹并非只有一道颜色,没有多元色彩,岂能在天空划出明艳彩桥,何况是言论新闻,更不应该由一党一人独霸?据。
以为一统江山唯我独尊,不过是权力的意淫。
??《彩虹并非只有一道颜色》? 文/潘永强
因为潘永强
1998 年前后算不算是一段火红的岁月?90年代末的马来西亚对我这个八字辈来说,是处于政治动荡的非常时期。潘永强是在九十年代末关键时刻“出现”,两千年继庄迪彭、黄进发后冒起成为马华政论新秀。潘永强当时候是《星洲广场》的主编,企图以舆论引导广大读者关注社会课题,潘氏新颖的观点、题材选择叱咤整个中文媒界,风头无人可及。每逢周日出版的《星洲广场》对我来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从政治到社会制度、民生议题到主义论争、民族民主人权等等,犹如启蒙冲击波般一浪接一浪,激荡着我开始思考的脑袋。每周日早上我必定打开《星洲广场》,赤足蹲伏向着晨曦,一字一句似懂非懂地囫囵吞枣,仿佛对着潘永强编的《星洲广场》进行礼拜。此时此刻,才想起房角某处的旧报纸堆里还有着当时的报章收集。想必它们已经发黄陈旧。不禁叹曰:时代虽不再,激情犹新矣。
连续这样连名带姓地多次“潘永强”称道,可说是非常不敬的。不是因为年少时对潘永强的崇仰,因为在大专时期曾经旁听过潘老师一个学期的“政治学概论”。那时候,大概是潘老师第一次开课,地点在新纪元学院,有幸受教者是媒体系学生。得悉潘永强来教学时,沈观仰老师同时也给我们开哲学课,一个是坐镇《南洋沙龙》的专栏作家、一个是《星洲广场》的舵主兼《民间》主编,虽然当时候同学们还得在货柜箱里上课,可是深感安慰,回绕脑里的一直是梅诒琦先生说的:“大学者乃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这样的想法简直就是太神话了潘沈等人。可是在一个贫乏的马华社会里,何处觅得一二知识分子来引领新生代思考?双十年华面向世界、面对人生社会,依然是空纸白卷一张,已经不能说是什么赤子单纯,而是一个不健全的教育制度下产生出来的无知愚寡。在一个简陋的课堂上奇迹般可以接触西方哲学、政治理论,是多么弥足珍贵啊。哲学课期末我交了一篇《浅析马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单面人”》,以马库塞单面人说法探讨了马来西亚社会中上层阶级的几个“单面人”现象。这是生平第一份哲学思考的粗浅结果,老师评价甚高,提出许多值得深入讨论的意见,让我欢欣不已。在不涉及任何学分或者分数的政治学概论课里,我遗憾自己没有交出任何探讨政治的文章让潘老师赐教。
潘老师一向以来形象都是温文儒雅,文质彬彬,带着浓厚的书卷味。确实,学者形象确实比现在的评论人形象来得鲜明。还记得潘老师上课归上课,看出来是用心备课,对马华公会或许还没有后来的关心爱护,火气不大。当然,政治课偶尔也需要一点冷风热嘲带动气氛,偏偏潘老师的长相天生不利于讲笑话,话里有话的时候让人都觉得很认真。政局风云莫测,政治领袖谋略开始张牙舞爪,牵一发而动全身,魔掌无处不在,直到媒体掌控。潘永强的文字也逐渐流露出火药味,那是一种按捺不了的急切,只因为一切荒诞不可睹的事件接踵而来,让人忍无可忍,包括潘永强,等人。受到严厉批判的包括代表华人的政党领袖、政治领导人、各种政策制度等等。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学界媒体界人事大流动,学者、知识分子、办报人、记者、时评人、讲师、写作人等,大家开始省思当下的位置所在,重新为自己定位。潘老师常说:有时候自我标榜一个口号,最后将是给自己沦为一个笑话。潘老师后来离开了报馆,投入华社研究中心。绕过茨厂街到陈氏书院,对面便是华社研究中心。那是我的高中时期玩耍的地方,特意千里迢迢从加影到陈氏书院补习就是为了在茨厂街玩。当时候还存在的“文化街”,从陈氏书院窜到海螺、大将书店,到Old China Cafe楼上看古董,然后一直到上海、商务、学林书局,一周玩两天,夕阳西下才回家。
华社研究中心其实就是雪华堂建筑的一角。后来雪华堂前建起了轻快铁,一把镰刀般铲过雪华堂建筑正门,隔开了门前壮观的人造大喷泉,从风水角度来说可说是十分凶煞,不利民族命运也!潘老师到华研上班编《人文杂志》的那段日子,看到中华楼那大杂院、看到那大煞风水的空中地铁、美化中的繁杂茨厂街,不知道有何感想。当时候我也准备出国念书了,带走的心情跟华社的心情一样,有点沉重还有更多的无奈。反复不断思考:我应该从此走得更远?还是应该早日归来?
临走前,我有一本梵谷绘图本的纪念册,请潘老师写几个字留念。记得他是写:可以跳出这个贫瘠的马华社会是好事,毕竟清华大学曾经有王国维、梁启超、叶公超以及陈寅恪云云。詹缘端老师写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还有其他老师的都不能清楚记得了。因为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我在宿舍里自行隔离,这本纪念册常常是我自我勉励的良师益友,把它放在枕头下,希望它会绽放力量。因为听谭家健教授说过:从前人们遇上疾病都会把《易经》以及文天祥的《正气歌》放在枕边。当然,这样的一本纪念册子是无法驱走非典病菌,但是异乡的求学日子需要很多自我鼓励的动力。尤其是一个人与世隔绝的时候。后来,校方突然要我们重新调房独立隔离,马上要我们大搬家,我和几个同学在父母的催促下匆匆回国了。我在收拾行李时竟然忘记了那一本枕下的纪念册。北京当时是一团乱,同学们都在自行隔离,通讯不方便,大家都不离开住所。我联系了同学请他回去原有的住处帮我找那本纪念册。可是情况太乱了,据说那所公寓进行了药物喷射、褥垫枕头都进行更换,等我再回京时,清华大学已经把那栋校外公寓转售出去了,留学生全部召回校内宿舍里住。我想起了那本可怜的纪念册,任由非典病毒侵入,如今不知所踪。依稀记得是潘老师蓝色原子笔的字迹,还有詹老师那隶书字体般的一行话。里面还有一页是张惠思老师留给我许德发先生的电子邮件。结果,统统随着那本册子弄丢了。
从《星洲广场》到后来的《东方日报?名家》,潘老师在我看来是马华有史以来最关心 “马华”的人。说什么“爱之深,责之切”可能很老土,可是怎么也无法怀疑潘永强文字里苦口婆心下的用心与真心。杨善勇在专栏里誉潘永强为“马华政论第一单打”,网络上的口水留言有人窜改周杰伦歌词成“三强二强潘永强”,这一切虽然诙谐滑稽,却也不过是人们对潘永强一路走来多次漂亮的奇招拍案叫绝,对他的高明见解啧啧称奇的表现。
我毕业回来后,潘老师人在新纪元学院的学术研究中心。新纪元学院秉持多元开放、自主自治的校风,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空气较为清新、流通的地方。潘老师除了持续编《民间》,还出版了第一本著作《马华政治散论》,依然是多产的报章专栏作者,看来他的心情十分愉快。我毕业回来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时尚杂志当记者,后来到电视台工作依然继续在时尚杂志的写作。之中有一个机会到马华公会终身学习执行秘书处工作,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黄家定给我批了信,由拿督黄思华完成聘用手续。对于投身政治的最后关头我犹豫不决,矛盾非常,之中挣扎也给大家都带来了麻烦。后来跟潘老师的一番交流后,因为潘老师说的一句话:你还是回去清华跟汪晖读书吧。最后,我拒绝了终身学习的工作。现在,我虽然人在时尚界工作,我从不花钱买时尚杂志,今天逛书局,偶然看到本地时尚杂志《FASCINO品味志》里竟然有潘永强的专栏“Easy Talk对话入座”,让我感到十分意外,毫不犹豫就把杂志买下来了。过后跟友人聊起:时尚杂志有潘永强的专栏,这本杂志的销量都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无论如何,我之所以会不想就掏腰包买下一本时尚杂志,也只因为潘永强。
24/5/2005
Post a Comment